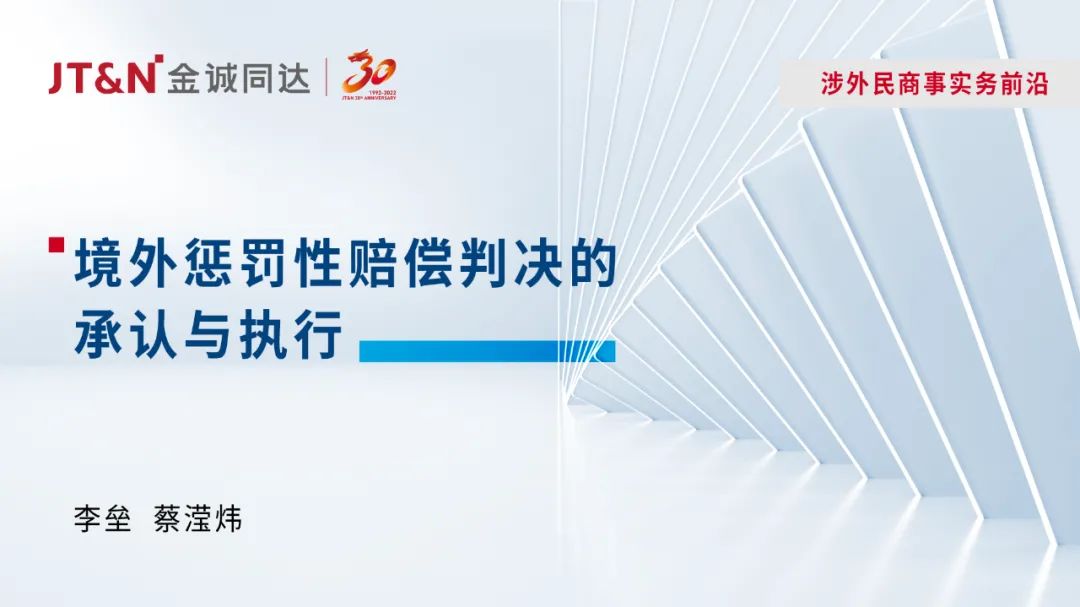
境外惩罚性赔偿判决的承认与执行
前言:2021年12月31日,最高人民法院印发《全国法院涉外商事海事审判工作座谈会会议纪要》,该纪要基于最高人民法院于2021年6月10日在南京召开了全国法院涉外商事海事审判工作座谈会,系统回顾总结2018年以来全国法院涉外商事海事审判工作情况,针对涉外商事海事审判工作中存在的前沿疑难问题作出相应规定,以统一裁判尺度。金诚同达律师所李垒律师和蔡滢炜律师将结合该纪要的新规定,撰写系列文章对纪要进行解读。
本系列第一篇《涉外民商事送达中的几个实务问题》、第二篇《涉外民商事诉讼协议管辖制度的实践及新发展》、第三篇《涉外仲裁市场的全面开放与法律障碍》、第四篇《境外法院商事判决承认和执行制度的新发展》此前已发布,本文为该系列文章第五篇。
惩罚性赔偿(Punitive Damages)制度发源于英国,发达于美国,目前采用惩罚性赔偿制度的国家主要有美国、英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加拿大、南非等。不过即使是在普通法系国家,惩罚性赔偿制度的应用范围和条件在不同国家也存在差异。2021年《全国法院涉外商事海事审判工作座谈会会议纪要》第45条首次明确了针对外国法院判决中惩罚性赔偿的审查制度,使得这个问题再次成为众人关注的焦点。
一、惩罚性赔偿制度的历史和发展
惩罚性赔偿制度源于英国,目前公认的第一个惩罚性赔偿案例是1763年的Wilkes v. Wood案 (Wilkes v. Wood, 98 Eng. Rep.489)。1964年英国上议院在Rookes v. Barnard案(Rookes v. Barnard, 1964 A.C. 1129)中确立了现代英国惩罚性损害赔偿的基本制度--惩罚性赔偿适用于三类案件:
- The defendant is guilty of oppressive or unconstitutional action (被告存有胁迫或违宪的行为);
- The defendant has calculated that the money to be made from his wrongdoing will probably exceed the damages payable(被告发现他从不法行为中获得的收益很可能会超过应付的损害赔偿金);
- Cases where statute authorizes an award of punitive damages (立法授权判给惩罚性赔偿金的案件)。
长期以来,英国法院原则上只在涉及故意侵权行为的案件中允许惩罚性赔偿,惩罚性损害赔偿在合同违约索赔中是不存在的。但作为例外情形,根据Rookes v. Barnard一案,在三种涉及合同的案件中也可以申请惩罚性赔偿:
- 违反保险诚信的案件:保险公司受到“诚信和公平交易契约”的约束,如果保险公司不守信用,他们可能要承担惩罚性赔偿责任;
- 某些侵权/违约竞合的案件:如果在合同环境中,一个独立的侵权行为因故意(而非疏忽)或鲁莽而导致损害,可能被判以惩罚性赔偿;
- 某些性质恶劣的欺诈案件。
美国是当代运用惩罚性赔偿制度最为成熟的国家。在美国,绝大部分州允许惩罚性赔偿,而且联邦层面也有包括《公平信用报告法》(The Fair Credit Reporting Act)、《克莱顿法》(Clayton Act)、《诈骗影响和腐败组织法》(Racketeer Influenced and Corrupt Organization Act)等立法明确规定了惩罚性赔偿救济。今天美国法院在涉及侵权法、合同法、财产法、海事法、劳动法和家庭法的诸多诉讼中,都被允许适用惩罚性赔偿。有些美国判决的惩罚性赔偿金额之高,达到令人震惊的地步。如1987年的Pennzoil Co. v. Texaco Inc.一 案[Pennzoil Co. v. Texaco Inc, 481 U.S.1 (1987)]陪审团支持了共计30亿美元的惩罚性赔偿金。
在美国侵权法下,被侵权可能获得的救济包括补偿性损害赔偿金(Compensatory Damages)和惩罚性赔偿金(Punitive Damages),但是否适用惩罚性赔偿金,法院拥有很大的自由裁量权,而且各州的成文法对惩罚性赔偿金的数额也有一定限制。
在合同领域,2002年的Whiten v. Pilot Insurance Co.一案中,美国最高法院对惩罚性赔偿金的适用条件作出了限制,即要求“违约方存在单独可诉的不法行为(independently actionable wrongs)”。法院在认定赔偿性惩罚金时,应分析当事人从合同的缔结到履行再到终止的过程中所有的行为,并将“单独可诉的不法行为”与其他行为进行区分,再认定这些“单独可诉的不法行为”造成的侵害是应该通过惩罚性赔偿金还是补偿性赔偿金进行救济。例如,在1989年Vorvis案中,原告Vorvis是被告公司的雇员,被告在未事前通知的情况下与原告解除了劳动关系。原告以“未通知即被解雇”违反劳动合同为由起诉被告,要求获得赔偿。除此之外,原告还主张惩罚性赔偿,因为原告在职期间受到上司不公正的待遇,导致精神压力过大,不得不接受住院治疗,而正是在住院治疗期间,原告遭到解雇。然而,法院认为,虽然原告原上司的行为确实非常过分,但由于他的行为不属于违反劳动合同的行为,即并非“单独可诉”,因此原告不得请求惩罚性赔偿金。原告如欲获得惩罚性赔偿金,则还需证明被告违反了其他原则性的合同条款,如善意义务(duty of good faith)条款。
二、传统大陆法系国家对惩罚性赔偿制度的抵制态度
传统上,大陆法系由于固守公私法二元理论,对违法行为的惩罚和对受害人进行救济是严格加以区分的,带有惩罚因素的责任被全部纳入到刑事责任或者行政责任的领域中去了,所以一直对民事诉讼中的惩罚性赔偿持拒绝态度。以德国为例,德国法院一直严格遵守《德国民法典》的规定,否认赔偿金具有惩罚或遏制的作用,在国际私法层面,德国法院也一直拒绝执行包含有惩罚性赔偿金的外国裁决。
1992年发生的一个案件具有代表性意义。当时一名14岁的美国女性在美国加州对一名德国被告提起了性虐待之诉。美国加州法院裁决给予原告400000美元的赔偿金,其中包含惩罚性赔偿。原告申请执行时发现被告已从加州迁居德国,并且在美国没有留下任何财产,于是便向德国法院申请执行。德国联邦最高法院认为,对该份判决中的医疗费、后续治疗费、因焦虑和伤痛等产生的损失部分均可以执行,但是对于其中的惩罚性赔偿不予执行。理由在于该份判决中的惩罚性赔偿与德国法中只赔偿原告遭受的损失的基本原则相违背,同时这也与德国法的公共政策相违背。
三、我国对惩罚性赔偿制度的有限引入
我国最早引入惩罚性赔偿制度的领域是消费者权益保护。1993年《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四十九条规定:“经营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有欺诈行为的,应当按照消费者的要求增加赔偿其受到的损失,增加赔偿的金额为消费者购买商品的价款或者接受服务的费用的一倍。”2013年修订后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五十五条规定:“经营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有欺诈行为的,应当按照消费者的要求增加赔偿其受到的损失,增加赔偿的金额为消费者购买商品的价款或者接受服务的费用的三倍;增加赔偿的金额不足五百元的,为五百元。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经营者明知商品或者服务存在缺陷,仍然向消费者提供,造成消费者或者其他受害人死亡或者健康严重损害的,受害人有权要求经营者依照本法第四十九条、第五十一条等法律规定赔偿损失,并有权要求所受损失二倍以下的惩罚性赔偿。”
我国引入惩罚性赔偿的还有知识产权保护领域。2018年11月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上的主旨演讲中提出,中国将引入惩罚性赔偿制度。此后,惩罚性赔偿制度的法律修订和政策制定工作加速推进。2019年修订的反不正当竞争法、2020年修订的专利法和著作权法等知识产权部门法均增加了惩罚性赔偿条款。此前,2013年修订的《商标法》、2015年修订的《种子法》就已经率先确立了惩罚性赔偿规则。2021年施行的《民法典》第1185条则总括性地规定了知识产权惩罚性赔偿制度,标志着惩罚性赔偿在知识产权领域实现了全覆盖。
此外,《民法典》还在1207条规定了产品责任侵权责任中的惩罚性赔偿,并在第1232条增加规定了生态环境侵权责任的惩罚性赔偿。
四、惩罚性赔偿的识别
从各国对惩罚性赔偿的定义看,“超越被害人实际所受损害”是惩罚性赔偿的基本特征。但是,各国对赔偿类型、构成要件和计算方式本身就存在差异,所以仅以“超过实际损害”为标准,不一定能准确界定惩罚性赔偿。例如大陆法系中的定金制度,其目的虽在于担保债务之实现,但现实中守约方的实际损失未必达到定金罚则的数额,而违约方很可能存在主观违约的恶意,此时定金罚则其实本身也带有惩罚、威慑违约方的功能。
一些大陆法系国家存在抚慰金制度,主要用于填补因侵权行为导致的非物质利益损害。在大陆法系国家看来,其并未超出“损害填补”的基本范畴,但在英美国家看来,这可能已经成为变相的惩罚性赔偿。
在一些大陆法系国家,法院有时会为制裁被告,或为弥补原告举证能力不足,或为平衡财产权益的不正当变动而作出“加重赔偿”。这种赔偿在美国会被认为类似于惩罚性赔偿,而在大陆法系国家则可能被认为是补偿性质的。在1994年的卡罗琳案中,德国法院判决一家虚构专访的德国小报向摩纳哥公主卡罗琳赔偿180,000马克,这是德国法院针对侵犯人格权给予的最高额赔偿。有德国学者将本案与同时期发生在美国的 Cher v.Forum International,Ltd.案对比后认为,“虽然采用了一种不同于损失赔偿金的方法,但是德国联邦最高法院采用相同的论证达到了美国法院判决的惩罚性赔偿金的效果……德国法院对于侵权赔偿的态度发生了转变。过去,侵权案件关注的重点是原告,即满足原告的需求。现在,侵权案件关注的重点转向被告,即遏制侵权人不再实施类似行为或防止将来发生类似行为。因此,这不再是传统观念中的赔偿和满足,而是更符合惩罚性赔偿的理念”。
五、《纪要》第45条的理解与适用
从本次《纪要》第45条的规定看,中国法院对惩罚性赔偿的识别采取了形式加实体两项标准。形式上,该判项应注明为“损害赔偿金”;实体上,其金额应明显超出实际损失。但在实际操作中,如果外国法院的判项中没有使用“损害赔偿金”,而是使用类似“补偿款”的措辞,但“补偿款”的金额同样明显超出实际损失,我国法院是否会将此类判项视为损害赔偿金,仍有待未来的相关案例予以明确。
从法理上分析,我国法院拒绝承认执行外国法院判决中的惩罚性赔偿,可能有两个深层的原因:一是违反我国法律下损害赔偿的补偿原则,二是可能损害我国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但我们认为这两个理由其实都有值得讨论之处。首先,《纪要》第45条未排除对知识产权、产品责任、生态环境类案件的适用,而我国已经在知识产权、产品责任、生态环境等领域引入了惩罚性赔偿制度,如果同样案件由我国法院管辖也会判决惩罚性赔偿,那么拒绝承认执行该案的外国法院判决,在逻辑上就不能自洽。另外,外国法院的判决也可能支持中国原告的请求,如果一概拒绝承认执行包含惩罚性赔偿的外国判决,在某些案件中反而可能损害我国当事人的权益。当然我们注意到,根据《纪要》第45条,中国法院“可以”对惩罚性赔偿裁定不予承认和执行,这显然意味着中国法院为具体案件留下了自由裁量的空间。
最后,我们认为《纪要》可能会对当事人的涉外案件协议管辖产生影响。因为《纪要》释放出一个信号,即如果一个外国法院的判决包括有惩罚性赔偿,以至于在中国法院看来造成了严重的不公平,中国法院有可能对惩罚性赔偿部分裁定不予承认和执行。这对某些案件的当事人来说,选择外国法院管辖的意愿可能会因此降低,甚至促使当事人放弃诉讼转而选择国际仲裁。
综合以上,我们认为《纪要》第45条针对惩罚性赔偿判决的可执行性审查提出了新的指引,是一个值得肯定的进步,我们同时期待未来真实案例的发生,以便人民法院得以在实践中进一步发展并完善我国的外国判决承认与执行制度。
来源:金城同达
编辑:梵高先生
本文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知产前沿立场,如有侵权,请联系小编删除

相关文章
|
关注公众号
|
联系小编
|
|
| 电话:+86 18917798290 | ||
| 地址:上海市嘉定区陈家山路355号创新创业大厦 | ||


 分享到微博
分享到微博 分享到微信
分享到微信 分享到领英
分享到领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