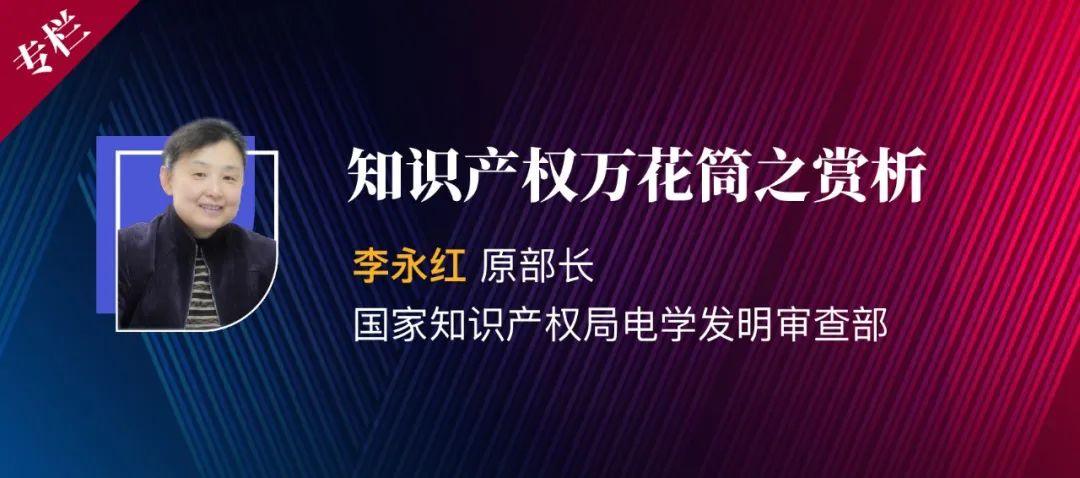
李永红 | 知识产权万花筒之赏析
“红”“绿”“黄”案之趣
读毛禾枫、薛佳琳律师撰写的《我国地理标志与商标的冲突问题及解决对策》,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三个不同颜色的案例。
一是“吉山红”与“吉山老酒”之争;二是“泰山绿”与“泰山绿茶”之争;三是“黎村黄”与“黎村三黄鸡”之争。
三个案例涉及的都是商标与地理标志的冲突。其中,三字标识都是注册的商标,而另一标识则均为在后注册的地理标志。
不同的是,三个案例中的被诉客体既有在先注册的商标,也有在后申请注册的地理标志;三个案件涉及不同的审级,不同的判断思路,不同的判断理由。
共同之处是,最终的胜券均落于在后注册的地理标志,而在先注册的商标或被判定无效或被判定不影响在后申请注册的地理标志。纯属偶然?亦或必然?不同判决理由背后又是否存在相互关联的逻辑?
相同的判决结果是否必然?
对此,文章没有直接断言。不过,文章中有一个值得注意的观点:“商标法保护模式以先申请原则和混淆可能性为基础,强调保护在先商标在诚信经营的过程中积累的商誉和市场影响力,而专门法保护模式所期望达成的目标是将地理标志作为某一地区或国家整体的文化遗产,即公有财产,故应当获得高于商标权这一私有财产权的法律地位。”
的确,商标权与地理标志权的一个重要差别是:商标注册人可以是自然人、法人或其他组织,而地理标志注册人则为地方政府成立或认定的管理机构;商标注册人对其注册的商标拥有占有、使用、收益、处分的权利,而地理标志注册人则主要负责地理标志产品的质量管理及允许满足地理标志条件的产品或服务的生产或服务商使用地理标志,其本身并不享有对地理标志占有、使用等权利。因此,前者具有纯粹的私权特点,而后者则具有鲜明的公权特色。
当这两种权利相互冲突而无它解之时,是恪守民法中在先权利优先的原则还是兼顾公权优先的政策考虑?文章从国外不同法域的立法司法实践到我国的国情进行了比较全面的研究与分析,值得拜读、思考。
不同判决理由是否互有关联?
上述三个案件中,出现了两个方向相异的判决理由:
一是判定二者相近似,如案件一。该案中,被诉客体是注册商标,引证客体是在先使用在后申请注册的地理标志,注册商标因与在先使用的地理标志相近似,故而“易误导公众”,经两审判决被判无效。
二是判定二者不相近似,如案例二、三。其中,被诉客体是申请注册地理标志,引证客体是在先注册商标。结论都是在先注册商标不影响在后地理标志的注册。判决理由略有差异。案例二的判决理由之一为:“引证商标在茶商品上缺乏显著特征,是否相似不构成地理标志注册的障碍。”案例三的判决理由之一则是:“由于“黎村黄”商标具有显著性,该商标的注册不能阻止该产地其他人使用‘黎村三黄鸡’等标识,”。
上述信息引发人们的疑问是,同样是以地名+色彩词的商标与地名+产品名的地理标志,为何认定此与彼相近似故而“易误导公众”而彼与此却被认定不相近似?
因未阅读所有判决的全文,故而无法也无意评述判决。但由此联想到专利新颖性判断中也有一种双向判断标准:如果权利要求限定某特定的金属如铜,而对比文件公开了“金属”,结论是二者不同;反之,若权利要求限定的是“金属”,对比文件公开了铜,结论则是二者相同。
因此,看到上述判决信息时,本能的反映是:界外人看似矛盾的现象背后,或许存在业内人能够理解的共同逻辑。这个逻辑似乎建立在两种权利的权能差异之上。
首先,在涉及权利冲突问题上,被冲突的权利是什么,与其权利功能密切相关。而在不同的权利功能语境下,即便采用相同的词汇如“相近似”、“混淆”或“误导公众”,其内涵也未必相同。
商标权的本质特征是通过显著性标识在商标注册者(生产者或服务商)与特定商品或服务之间建立联系。即便集体商标、证明商标允许在特定条件下包含地名,也未改变上述权利属性。因此,在判断是否(可能)侵犯商标权时,关注的是商品来源标识意义上的混淆。比如,对于消费者而言,三字的“吉山红”是否易于混同于四字的“吉山老酒”?是否易于联想到二者出自或关联于同一厂家?
另一方面,地理标志则通过明确的地名与产品或服务的通用名称在某类产品或服务与其所关联的地理区域之间建立联系。因此,在判断是否(可能)侵犯地理标志专用权时,关注的则是商品源于何地意义上的混淆。比如,当二者均含有地名“吉山”,且产品均为酒类,是否会导致公众对产地相同的联想?
另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是,一般而言,判定商标标识本身构成“相近似”,足以得出商标侵权的结论。而判定是否侵犯地理标志,仅确定标识本身 “相近似”尚不足以画上句号。更为实质的判定是,被控侵权的产品来自于何处。
根据《商标法》第四条,“以地理标志作为证明商标的,其商品符合使用该地理标志条件的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可以要求使用该证明商标,控制该证明商标的组织应当允许。”“以地理标志作为集体商标的,其商品符合使用该地理标志条件的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不要求参加以该地理标志作为集体商标的团体、协会或者其他组织的,也可以使用该地理标志,该团体、协会或者其他组织无权禁止。”
尽管上述规定并非来自于有关保护地理标志的规定。但作为与地理标志相关的法律规定,至少具有法理上的可借鉴性。
据此,如果被告产品来自于吉山且满足相关产品质量、特色的要求,则两个标识本身是否“相近似”甚至是否相同,都不会导致对地理标志专用权的权利冲突。
到此,读者可能也看出万花筒的趣味了。当转到权利主体的观察角度时,或许看到的是公权与私权的高下之分;而转到权利功能的角度,看到的则是两种权利的左右之别。
就主观愿望而言,笔者更希望看到二者并行不悖的局面。毕竟,二者的关系链中虽然都有产品或服务,但范围不同,一是特定商品(如牛栏山酒厂制作的某种白酒),另一是某类商品(如白酒);链条的指向也各有不同,一是指向特定生产或服务商,二是指向某地理区域。
所以,二者并不必然相斥。合理合法地行使各自的权能,并行不悖地发挥各自的资源优势,也许更值得期待。
因此,避免二者权利冲突的另一进路是,探索共存且不冲突的方式。
比如,通过规范标识的表达,或可使二者相互区别。如同药品中商品名与通用名泾渭分明。各自代表着对特定药品的指向与对同类药品的统一规范。
司法实践中也不乏出现采用略改名称,以示区别的做法。
对此,注册人、行政、司法甚至立法上可能都有努力的空间。若上下协同,你死我活的抉择或可在一定程度上转为携手共进的和谐。想到此,我乐观地画上了本文的句号。
作者:李永红
编辑:Sharon

相关文章
|
关注公众号
|
联系小编
|
|
| 电话:+86 18917798290 | ||
| 地址:上海市嘉定区陈家山路355号创新创业大厦 | ||


 分享到微博
分享到微博 分享到微信
分享到微信 分享到领英
分享到领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