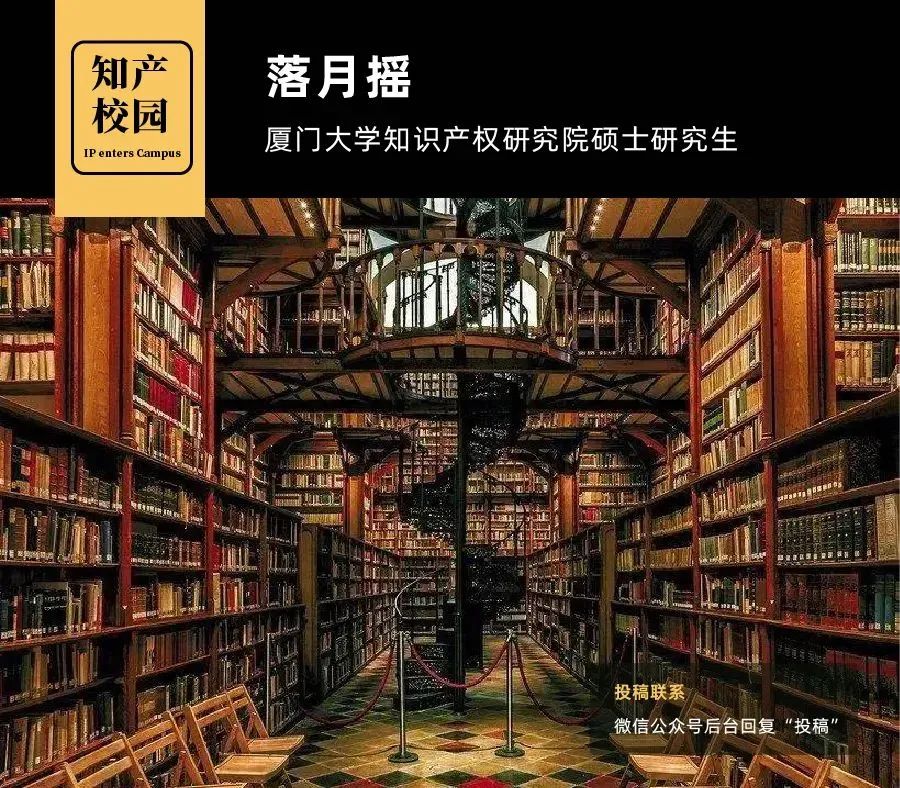
知产时评 |《谭谈交通》一案中的五个法律问题
7月11日,上游新闻报道了原告的起诉状、授权委托书、版权声明等。为应对舆论压力,成都市广播电视台委托四川君盛律师事务所发布律师声明,声明中称不存在对个人“索赔千万”的情况,完全为依法维权。本文就该案中涉及的几个重要问题展开讨论,主要基于网上披露的相对可信的文件中记载的事项。如有其它证据,则应另行分析讨论。
重点导读
一、本案应当适用的主要法律
二、《谭谈交通》的作品类型
三、《谭谈交通》的权利归属
四、原告的权利基础与身世
五、《刑法》介入的可能性
结语
本案应当适用的主要法律
法律问题的分析应当基于有效的法律与通行的法理,有效的法律往往指事件发生时应当适用的法律。成都市广播电视台委托四川君盛律师事务所发布的律师声明中称,“2005年3月起,在成都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的指导下,成都市广播电视台都市生活频道策划、编导、制作并播出《谭谈交通》节目,该节目由成都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指派时任交警的谭乔进行现场主持。节目于2018年5月停止更新,谭乔于2021年8月辞去公职。”成都市广播电视台的版权声明称,《谭谈交通》自2005年3月28日至2006年6月4日期间在都市生活频道《平安成都》栏目中播出,之后经过几次版块整合与扩版。2021年9月26日停播。成都市广播电视认为其具有《谭谈交通》的全部版权。
明确应适用的《著作权法》对作品类型的认定与著作权归属的判断有影响。我国《著作权法》1990年颁布后,经历2001年,2010年,2020年数次修订。本案跨越了数次法律修订后的生效期间。《谭谈交通》节目自2005年3月28日开播,于2018年5月停止更新。因此本案中相关问题的讨论适用的法律依据主要应为2001年修订的《著作权法》,尤其是对作品类型的认定与著作权归属的判断。如果侵权行为发生在修改后《著作权法》生效实施日之后的,则应当适用相应的修改后处于生效期间的《著作权法》。
《谭谈交通》的作品类型
在讨论《谭谈交通》的作品类型前,有观点为谭乔给出的抗辩参考意见认为,《谭谈交通》不构成作品,而属于时事新闻,因此不适用《著作权法》。但该意见稍显牵强,谭乔作为交警和主持人拦下一些涉嫌违反交通法规的路人,在聊天访谈,引起民众的关注与共情之间,实现普法宣传。作品的独创性可以说有目共睹,若只是普通“时事新闻”,又为何能远比其他时事新闻受到追捧赞赏。《谭谈交通》应当属于著作权法意义上的作品。
根据2001年《著作权法》(第3条第6项),《谭谈交通》应属于以类似摄制电影的方法创作的作品,严格来说不应称之“视听作品”。“视听作品”属于2020年《著作权法》修订后的法律概念,在此之前的《著作权法》中并无这一类型的作品。当然此后同类型的作品可以归入这一概念。
《谭谈交通》的权利归属
判断《谭谈交通》的著作权归属是本案的焦点问题。对涉案作品著作权的归属,目前主要有两类观点:一是认为属于成都广播电视台和成都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共同享有;二是认为属于成都广播电视台和自然人谭乔共同享有。少有观点认为成都广播电视台可以独自拥有完全版权。
本文认为,如果各方当初不存在对《谭谈交通》著作权归属的约定,那么该作品的著作权应由成都广播电视台和谭乔共同享有。
根据2001年《著作权法》第15条的规定,[1]以类似摄制电影的方法创作的作品的著作权由制片者享有,但编剧、导演、摄影、作词、作曲等作者享有署名权,并有权按照与制片者签订的合同获得报酬。
需要注意到,编剧、导演等成员与制片者之间属于雇佣关系。这些成员在广义上虽可以称为制片者的合作者,但并不适用该法13条关于作品合作创作的规定。[2]但制片方完全可能存在符合该法13条规定的其他合作者。此时除非另有约定,制片方不可能独自享有著作权。
前文提及的律师声明中提到:2005年3月起,在成都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的指导下,成都市广播电视台都市生活频道策划、编导、制作并播出《谭谈交通》节目,该节目由成都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指派时任交警的谭乔进行现场主持。显而易见的是,谭乔在《谭谈交通》节目中的“主持”有别于传统综艺节目中的依照台本进行的主持,付出了较多的智力劳动,有较为鲜明的个人特点,否则也不至如此风靡。或许单从作品名称“谭谈交通”中,便可发现谭乔在其中的重要性。
谭乔的创作行为属于完成工作任务的行为,应将该作品认定为职务作品,根据2001年《著作权法》第16条的规定,[3]谭乔应为著作权人。原因有二:一是谭乔受单位指派而参与《谭谈交通》节目,二是《道路交通安全法》(2003)第6条已明确规定,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及其交通警察执行职务时,应当加强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的宣传。[4]足以说明谭乔的行为应属于完成工作任务的行为。
综上所述,成都广播电视台和谭乔应共同享有《谭谈交通》的著作权。
原告的权利基础与身世
该事引发广泛关注后,该案的原告同样引起网友的注意。成都游术公司成立于2018年7月11日,并非涉案作品的原始著作权人。有知情人士向上游新闻记者提供了成都广播电视台向成都游术文化传播有限公司的授权书,其中显示,“成都广播电视台将《谭谈交通》的所有著作财产权以及将上述权利的转授权权利,以及将上述权利许可第三方进行分销的权利转授给游术文化”。“上述权利均为不可撤销的权利。”该协议中特别注明,转让的权利包含赔偿权。凤凰网《风暴眼》还公布了一份名为《关于就成都市广播电视台《红绿灯》栏目进行版权服务的策划方案》,对维权后的所得提出分配比例建议,目前该文件的真伪尚未得到证实。
该公司成立4年,总共提起了90余起诉讼,每一年的年报信息都显示社保缴纳人数为0。很显然是专为批量维权成立的空壳公司。单纯从法律技术上来说并无不妥,而且也并非其首创。7月13日,谭乔的微博又发了几份授权委托书的照片,成都市广播电视台将涉案作品相关权利及事项授权委托成都妹子文化传媒有限公司,而成都妹子文化公司再次委托给北京析言产权代理公司。层层嵌套的目的暂时未知。而公众目光的聚焦点已经开始转向这些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与成都市广播电视台内部人员是否有联系,受托人取得相关权利是否合法合规,是否依照法律程序进行。对于这些质疑,成都市广播电视台或许更有必要及时回应。
《刑法》介入的可能性
我国刑法规定了侵犯著作权罪,[5]谭乔在其发布微博中称可能面临牢狱之灾。本文认为本案应无刑法介入的可能性,谭乔应该未构成犯罪。原因有二,一是依照前文所述,谭乔应当享有涉案作品的著作权,自然不可能涉嫌侵犯著作权罪;二是根据谭乔公布的相关证据来看,其主要出于宣传交通安全知识、普及法律法规等目的使用涉案作品。难以认定主观营利意图。
结语
《谭谈交通》一案又一次引起人们关于知识产权权利滥用,版权流氓等现象的关注。对于明显的知识产权滥用行为有必要从制度层面加以规制,需要考虑从各方面遏制知识产权流氓的泛滥。而在一些案件中,权利人认为自身是正当维权,被告认为原告是滥用权利,正当维权与滥用权利的边界需要司法机关为社会公众厘清。此外,此次事件导致一系列侵权或不侵权的二创作品下架,关于视听作品等的合理使用问题同样是值得研究的重点。
注释(上下滑动阅览)
【1】电影作品和以类似摄制电影的方法创作的作品的著作权由制片者享有,但编剧、导演、摄影、作词、作曲等作者享有署名权,并有权按照与制片者签订的合同获得报酬。
电影作品和以类似摄制电影的方法创作的作品中的剧本、音乐等可以单独使用的作品的作者有权单独行使其著作权。
【2】第十三条 两人以上合作创作的作品,著作权由合作作者共同享有。没有参加创作的人,不能成为合作作者。
合作作品可以分割使用的,作者对各自创作的部分可以单独享有著作权,但行使著作权时不得侵犯合作作品整体的著作权。
【3】第十六条 公民为完成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工作任务所创作的作品是职务作品,除本条第二款的规定以外,著作权由作者享有,但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有权在其业务范围内优先使用。作品完成两年内,未经单位同意,作者不得许可第三人以与单位使用的相同方式使用该作品。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职务作品,作者享有署名权,著作权的其他权利由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享有,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可以给予作者奖励:
(一)主要是利用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物质技术条件创作,并由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承担责任的工程设计图、产品设计图、地图、计算机软件等职务作品;
(二)法律、行政法规规定或者合同约定著作权由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享有的职务作品。
【4】第六条 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及其交通警察执行职务时,应当加强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的宣传,并模范遵守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
【5】第二百一十七条 【侵犯著作权罪】以营利为目的,有下列侵犯著作权或者与著作权有关的权利的情形之一,违法所得数额较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或者单处罚金;违法所得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一)未经著作权人许可,复制发行、通过信息网络向公众传播其文字作品、音乐、美术、视听作品、计算机软件及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作品的;
(二)出版他人享有专有出版权的图书的;
(三)未经录音录像制作者许可,复制发行、通过信息网络向公众传播其制作的录音录像的;
(四)未经表演者许可,复制发行录有其表演的录音录像制品,或者通过信息网络向公众传播其表演的;
(五)制作、出售假冒他人署名的美术作品的;
(六)未经著作权人或者与著作权有关的权利人许可,故意避开或者破坏权利人为其作品、录音录像制品等采取的保护著作权或者与著作权有关的权利的技术措施的。

相关文章
|
关注公众号
|
联系小编
|
|
| 电话:+86 18917798290 | ||
| 地址:上海市嘉定区陈家山路355号创新创业大厦 | ||


 分享到微博
分享到微博 分享到微信
分享到微信 分享到领英
分享到领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