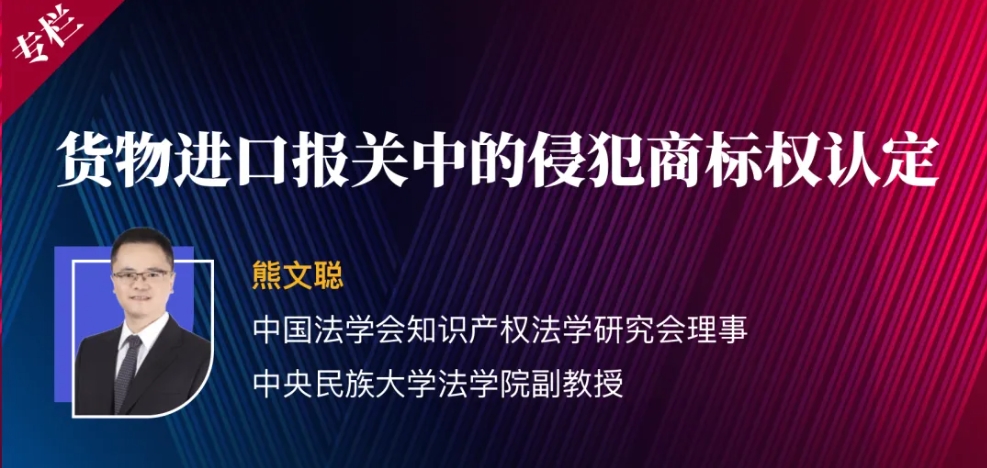
熊文聪 | 货物进口报关中的侵犯商标权认定
目次
· 引言
一、在报关单上注明品牌标识是否构成商标性使用?
二、商标权人是否享有进口权?
三、进口环节的帮助侵权应如何认定?
· 结语
· 引 言
随着跨境交往和国际贸易的日渐频繁,与商标权相关的跨境法律纠纷也逐年增多。但众所周知,商标权具有非常明显的地域性,承载着很强的国家意志。如何在国际贸易自由化与商标权严格保护之间做好平衡,是摆在立法者、司法者和执法者面前亟待回应的课题。例如,在报关单上使用涉案商标标识是否构成商标性使用;商标权人是否享有进口权;为进口侵权商品提供便利条件的帮助侵权应如何认定等疑问,均需要在法理、规范和逻辑上加以明确与澄清,以便于实务界正确理解和适用法律。
一、在报关单上注明品牌标识是否构成商标性使用?
在“奥提瓦v.乾盛数贸”侵犯商标权纠纷案中,一审法院指出:“乾盛数贸公司在报关单使用‘Neurio纽瑞优乳铁蛋白调制乳粉’字样作为商品名称进行报关的行为,起到了识别商品来源的作用,属于商标意义上的适用。该报关单所使用的‘纽瑞优’字样与奥提瓦公司的第25797592号、第6114540号注册商标‘纽瑞优’构成相同;‘Neurio’字样与奥提瓦公司的第61116472号‘Neurio’注册商标构成相同,与第25792637号‘Neurie’构成近似;在商品类别上,案涉侵权产品乳铁蛋白调制乳粉,与第25797592号、第25792637号核定使用商品‘婴儿奶粉’,与第61114540号、第61116472号核定使用商品‘奶粉’在产品原料、功能用途、销售渠道、销售对象等方面均相同,故构成相同商品。因此,该行为属于侵犯商标权的行为。”[1]然后,二审法院却认为:“乾盛数贸公司基于报关的要求填写报关单说明其所报关的商品来源于商标权利人这一真实信息,即乾盛数贸公司填写报关商品品牌名称所指示的是该商品的真实来源,该种使用行为系善意且合理的,不能传达导致消费者产生混淆的信息,故不构成商标侵权。”[2]可见,一二审法院针对同一被诉行为,却得出了两个截然相反的结论,体现了对何谓“商标性使用”这一概念存在认识上的偏差。管见认为:
首先,现行《商标法》第四十八条明确规定:“本法所称商标的使用,是指将商标用于商品、商品包装或者容器以及商品交易文书上,或者将商标用于广告宣传、展览以及其他商业活动中,用于识别商品来源的行为。”可见,一切将相同或近似的商标标识使用在商业活动中,用于识别商品来源的行为,都构成商标性使用或商标意义上的使用。而将与涉案注册商标相同或近似的商业标识(如“纽瑞优”“Neurio”)体现在报关单中,用于申报海关检查和征税,其最终目的是为了通过海关检查从而顺利进入中国市场销售该批货物。这显然属于一种典型的商业活动,即便该行为并没有明确列举在现行《商标法》第四十八条之中。《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进出口商品规范申报目录》中列明,针对“供婴幼儿食用的零售包装食品”和“配方奶粉”,其报关单中体现的申报要素不仅必须载明品名、成分含量、用途,还必须载明包装规格和品牌(中文或外文名称)。而很显然,“品牌”在法律上的规范表述即商标。
针对前述案件二审判决所主张的“善意且合理”地使用他人商标不构成侵权的观点,管见认为:
第一,关于“善意且合理”使用他人注册商标,现行《商标法》只规定了一种情形,即“注册商标中含有的本商品的通用名称、图形、型号,或者直接表示商品的质量、主要原料、功能、用途、重量、数量及其他特点,或者含有的地名,注册商标专用权人无权禁止他人正当使用。”[3]而很显然,无论是“纽瑞优”还是“Neurio”,都不属于直接表示配方奶粉或乳铁蛋白调制乳粉质量、主要原料、功能、用途、重量、数量或及其特点的标志,更不属于这类商品的通用名称或通用型号,故根本谈不上正当且善意使用。
第二,现行《海关法》第四十四条明确规定:“海关依照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对与进出境货物有关的知识产权实施保护。需要向海关申报知识产权状况的,进出口货物收发货人及其代理人应当按照国家规定向海关如实申报有关知识产权状况,并提交合法使用有关知识产权的证明文件。”可见,无论是海关申报人还是货物收发货人及其代理人,都负有最基本的不侵犯他人知识产权的审查义务和注意义务。并且,这里的知识产权,指的是进口国的知识产权,如进口国的注册商标专用权。因此,即便涉案标识在发货人所在国由另一主体享有商标权,向中国海关申报的货物收发货人及其代理人也有义务审查报关单及进口货物外包装上的商标或品牌标识是否侵犯了我国的注册商标专用权,其不能以已经获得了发货人或境外商标权人的授权同意而免责,更谈不上这种使用行为系善意且合理。
第三,现行《商标法》第六十四条第二款规定了“合法来源抗辩”制度,即“销售不知道是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的商品,能证明该商品是自己合法取得并说明提供者的,不承担赔偿责任。”但很显然,报关人和货物收发货人及其代理人并不适用“合法来源抗辩”。因为:其一,报关人和收发货人及其代理人并非商品的销售者,商品的所有权并未在其手上经过两度移转,其也没有为受让货物所有权支付合理对价。其二,无论是根据商业常识、交易习惯还是根据前述《海关法》的明确规定,报关人和收发货人及其代理人均具有基本的不侵犯他人知识产权的审查义务和注意义务,他们的法定职责、专业能力和实务经验决定了他们不可能不知道或理应知道经其手进口的货物是否涉嫌侵犯他人注册商标专用权,故无法援引《商标法》第六十四条第二款免责。
二、商标权人是否享有进口权?
前述“奥提瓦v.乾盛数贸”案二审判决进一步认为:“我国《商标法》关于商标侵权行为的规定中并没有将进口行为作为侵权行为予以规制,而《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则将进口行为作为专利侵权行为的种类予以明确,故在法律无明确规定的情况下,不能将进口行为认定为商标侵权行为,同时亦不能将进口行为视为商标使用行为变相认定构成商标侵权。”[4]管见认为,该观点与现行《商标法》的明确规定和基本法理不符,值得商榷。
第一,现行《商标法》的确没有像《专利法》那样直接而明确地将“进口”行为交由商标权人所控制。但这不能依照“法无明文禁止则自由”即可当然推出——进口涉嫌侵犯他人商标权的商品或货物的行为便是合法的、是不受法律追究的。因为《商标法》明确规定,但凡不属于法定的侵权抗辩事由(如前述描述性合理使用、合法来源抗辩等),便理应受到《商标法》第五十七条的规制。特别是其中第(一)项和第(二)项明确规定“未经商标注册人的许可,在同一种商品上使用与其注册商标相同的商标的”行为和“未经商标注册人的许可,在同一种商品上使用与其注册商标近似的商标,或者在类似商品上使用与其注册商标相同或者近似的商标,容易导致混淆的”行为,均属于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的行为。
而很显然,进口行为之所以会侵犯他人商标权,一定要么是未经许可在完全相同的进口商品上使用了与他人注册商标完全相同的商品;要么是未经许可在同一种进口商品上使用了与注册商标近似的商标,容易导致混淆;要么是未经许可在类似的进口商品上使用了与注册商标相同或近似的商标,容易导致混淆。可见,《商标法》规制的是未经许可使用他人注册商标,容易导致混淆的行为,而该使用商标行为在货物进口环节,与商品进口行为又是密不可分的,故进口行为无疑要受到是否侵犯他人商标权的检视,或者说商标权人有权控制他人将未经许可贴附了与其相同或近似的商标的商品予以进口是有明确的法律依据的。
第二,《专利法》之所以明确规定专利权人享有进口权,是因为专利权所保护的对象可以被直接描述为具体有形有体的产品,而商标显然不是具体有形有体的产品,但这并不妨碍商标权人可以控制他人将涉嫌侵犯其商标权的商品投入市场流通环节,因为商标和商品是一体的,所谓“使用商标”,一定是将载有商标的商品投入市场流通,否则《商标法》第五十七条第(三)项赋予商标权人有权控制或禁止他人销售侵犯其注册商标专用权的商品,便成了无源之水。法律举重以明轻,既然销售侵权商品的行为不被商标法所允许,作为同样重要的市场流通环节,进口侵权商品当然也不被商标法所允许。因为一旦“进口”环节没有控制住,让侵权商品真正进入本国销售和流通市场,对商标权人造成的损害往往是难以挽回的。
第三,严格来讲,虽然在单纯的进口报关环节,消费者及相关公众尚未看到涉嫌侵权的商标及商品,尚未给商标权人造成实际损害后果,但商标权人仍然享有“防范于未然”“将侵权行为扼杀在摇篮里”的权利,这是注册商标专用权是对世权、绝对权的当然体现,即其不仅包括损害赔偿请求权,更包括停止侵害请求权和侵害预防请求权。退一万步讲,即便《商标法》没有明确规定进口权,与《商标法》同为我国基本法律的《海关法》,其前述第四十四条也明确规定了货物进口行为要严格尊重他人的知识产权。
三、进口环节的帮助侵权应如何认定?
“奥提瓦v.乾盛数贸”案二审判决还主张:“被诉侵权产品在纸箱外包装、罐体中心、罐盖、罐体二维码中间处使用‘Neurio’标识的并非系由乾盛数贸公司所实施,因被诉侵权产品从国外进口时即带有前述包装样式,故该行为的实施不能归责于乾盛数贸公司”;“侵犯商标权行为的帮助行为,属于帮助侵权行为,该行为在主观方面应该是故意,过失不构成该项侵犯商标权的行为。主观上的故意是指明知为侵犯商标专用权的行为仍然提供便利条件,如因过失而未能得知为侵犯商标权行为而提供便利的,则不构成帮助侵权。本案中,因奥提瓦公司与珊妮娅公司对内存在商标争议由来已久,乾盛数贸公司作为贸易公司主要负责向海关申报进口并提供临时仓储等服务,其主要就提供前述服务而准备相应的申报材料。即使乾盛数贸公司仅提供了涉案货物进口的合同、形式发票等单据材料,而未提交涉案产品知识产权相关情况的材料,其行为仅系未尽到合理注意义务,在本案中并无相应证据证明乾盛数贸公司知晓被诉侵权行为系侵权行为而仍然提供便利条件,故乾盛数贸公司在主观上并不构成故意,其行为不属于商标侵权行为的帮助行为”。[5]管见认为,该观点同样值得商榷。
首先,笔者曾撰文指出,区分知识产权的直接侵权与间接侵权(如帮助侵权、引诱侵权或替代侵权等)的关键要件不在于直接侵权人与间接侵权人的主观过错(有无主观过错以及是过失型过错还是故意型过错)有何不同,而在于二者对于最终造成侵权损害结果的原因力及因果关系有所不同。[6]直接侵权的原因力是必然的、决定性的、首当其冲的,而间接侵权的原因力则是或然的、非决定性的,但又是不可忽略的。
其次,结合货物进口语境来说,虽然报关人及货物进口商可能不是该批进口侵权货物的制造者,甚至也不是将涉案侵权标识贴附于货物外包装上或罐体二维码中的直接实施者,但毫无疑问,正是该报关人及进口商的报关进口行为,才使得该批侵权商品第一次(初始)进入中国商标权人享有排他权的司法辖区(或“中国境内”),故该行为对于最终侵权损害结果的发生是决定性的、首当其冲的,是报关人及进口商基于自己的意志所实施的,故这不是帮助型间接侵权,而是直接侵权。这就好比,某作者完成了一部抄袭之作,将其投给某出版社,该出版社未经审查直接将该抄袭之作复制发行,该出版社承担的是直接侵权责任而非间接侵权责任,道理是一样的。
最后,退一万步讲,即便认为报关人及进口商只是为直接侵权提供便利条件,认定其承担帮助型间接侵权责任的主观要件也不是故意,而是知道或应当知道(或未尽到合理注意义务)。过失与故意的区分,对于民法中侵权人主观过错的认定,向来都是毫无意义的。但凡行为人未尽到合理注意义务,便可认定其具有侵权主观过错。故意与否,仅仅是对侵权主观过错程度定量的分析,而非定性的判断,仅仅对是否由侵权人承担惩罚性赔偿责任有影响。虽然现行《商标法》第六十三条第一款对于惩罚性赔偿的适用以侵权人存在主观“恶意”为要件,但之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侵害知识产权民事案件适用惩罚性赔偿的解释》第一条明确规定:“本解释所称故意,包括商标法第六十三条第一款和反不正当竞争法第十七条第三款规定的恶意。”
· 结 语
综上所述,从《商标法》《海关法》及相关行政法规和司法解释的字面表述及背后法理可以毫无疑义地得出,在报关单上标明进口货物的品牌,属于典型的商标性使用。同时,进口权是我国注册商标专用权人享有的一项明确的、法定的排他性权利,一切未经许可地将涉嫌侵权商品通过报关予以进口的行为,都属于直接侵权行为,报关人及进口商只要未尽到合理的审查和注意义务,便应当由其承担直接侵权责任。司法机关理应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作出令人信服的、经得起推敲的合理正确裁决,使得法律的权威和公平正义得以彰显。
注释(上下滑动阅览)
【1】四川自由贸易试验区人民法院(2023)川0193民初13706号民事判决书。
【2】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2025)川01民终814号民事判决书。
【3】参见《商标法》第五十九条。
【4】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2025)川01民终814号民事判决书。
【5】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2025)川01民终814号民事判决书。
【6】参见熊文聪:《被误读的专利间接侵权规则——以美国法的变迁为线索》,载《东方法学》2011年第1期。
作者:熊文聪
编辑:Sharon

相关文章
|
关注公众号
|
联系小编
|
|
| 电话:+86 18917798290 | ||
| 地址:上海市嘉定区陈家山路355号创新创业大厦 | ||


 分享到微博
分享到微博 分享到微信
分享到微信 分享到领英
分享到领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