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快讯 | 北京互联网法院开庭审理全国首例涉及AI绘画大模型训练著作权侵权案;进购“三无”表带后印上华为商标提价售卖2人获刑
1.北京互联网法院开庭审理全国首例涉及AI绘画大模型训练著作权侵权案

随着AI技术发展和新商业模式的应用,AI绘画逐渐走入公众视野——用户只用输入关键词和相应指令,AI绘画软件就能自动生成精美的手绘风格画作。聪明的AI离不开海量数据作为训练素材,供机器进行深度学习,在采集、复制数据和将数据作为训练语料“投喂”AI模型的过程中,相应的著作权问题广受关注。6月20日,北京互联网法院在线开庭审理了四起画师起诉AI绘画软件开发运营者的著作权侵权案件。
四起案件的原告均为插画师,同时也是某内容分享平台的注册用户,自注册该平台账号以来,长期发布其创作的绘画作品。四起案件的原告发现,有用户在该平台上发布了带有明显模仿原告作品痕迹的图片,这些用户均表示这些图片系通过某AI绘画软件创作。原告进一步查询获知,涉案某内容分享平台上线了该AI绘画软件。此外,涉案AI绘画软件在该分享平台上亦有官方主页,并自称“某内容分享平台(该平台名字)AI”。

原告认为,根据涉案AI绘画软件用户协议、宣传推广资料可认定其为北京某科技公司、上海某科技公司(以下简称被告一、二)及某内容分享平台运营者(以下简称被告三)三被告共同开发运营,三被告未经原告允许,将原告作品用于训练AI模型并应用于商业用途,已经远超合理使用范畴,共同对原告权益造成严重侵害。原告主张,被告抓取原告作品输入AI模型的行为,侵犯了原告的复制权;涉案AI绘画软件提供原告作品与其他图片杂糅、混合产生新图的技术服务,侵犯了原告的改编权;被告行为还侵犯了原告的作品作为物料训练AI的权利。涉案AI绘画软件习得原告作品的绘画风格后,“一键生成”的大批量图片可以轻松替代原告一笔一划绘制的作品,残酷挤压原告依托其作品获得收益的空间,对原告作品未来的市场造成毁灭性打击。因此,被告应当停止对原告著作权的侵害,包括但不限于停止在AI模型中使用原告作品、剔除模型中与原告作品相关的学习成果等,并赔礼道歉和赔偿原告经济损失。
被告一、二辩称,第一,原告诉讼请求不明确;第二,原告主张权利的作品与涉案AI生成图片不存在实质性相似;第三,被告大模型训练行为即使使用原告作品亦应构成合理使用;第四,被告尽到了提示义务。综上,被告一、二行为不构成侵权。
被告三辩称,原告以被告三运营的某内容分享平台的用户协议条款为切入点,推测被告三将原告发布于某内容分享平台的作品提供给被告一、二,该主张无事实依据。被告三未实施任何涉案争议行为,与其他被告各为独立的法律主体。涉案某内容分享平台用户协议条款是内容分享平台常见的通用条款,并不具有特殊性和唯一性,亦不存在原告主张的目的或情形。原告同样接受了其他平台与本案中某内容分享平台用户协议条款实质相同的其他平台用户协议,并在上述其他平台发布其在本案中主张权利相同的美术作品,更提供了原图下载。换言之,原告主张权利的作品在多个相同性质的内容分享平台公开发布、提供下载,某内容分享平台不具有特殊性和唯一性。因此。综合某内容分享平台用户协议条款作为通用条款的普遍性和一般性,以及原告多平台公开发布并提供下载其创作的美术作品,一方面,原告主张并无证据支撑;另一方面,被告三客观上并未向被告一、二提供本案系争的美术作品,亦没有实施涉案争议行为,不论从何种角度,被告三均不应承担任何法律责任,请求法院驳回原告全部诉讼请求。

原告是否享有主张作品的著作权?被告三是否是适格被告?被诉侵权行为是否存在,是否构成侵权或合理使用?如构成侵权,侵权的内容如何确定?侵权责任又应如何承担?庭审中,诉辩双方围绕上述争议焦点进行了举证质证和法庭辩论。原告申请技术辅助人员出庭,就AI大模型训练相关技术问题进行了说明。
目前,该案正在进一步审理中。(来源:北京互联网法院)
2.进购“三无”表带后印上华为商标提价售卖,2人涉案两百多万元获刑

涉案假冒表带
均为虹口区检察院 供图
两人购买激光打印机,给“三无”表带刻上华为商标,非法经营数额超过250万元。
6月20日,澎湃新闻记者从上海市虹口区人民检察院(以下简称“虹口区检察院”)获悉,经该院提起公诉,法院以假冒注册商标罪判处涂某某有期徒刑四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四十万元;判处张某乙有期徒刑一年九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六万元。
“我从一个朋友处听说,做假冒华为品牌商标比较赚钱”,机缘巧合下,涂某某萌生了销售假冒华为品牌商标产品的想法。于是,有空调销售经验的他开起了网店,对外销售假冒华为品牌手表表带。
2022年5月至2023年5月,涂某某伙同张某甲(另案处理)在未取得商标权利人授权的情况下,在广东省韶关市的一民房内设立小作坊。他们从电商平台购买无注册商标的表带,用自购的激光打印设备给这些表带印上了华为品牌的注册商标,然后在几家知名的电商平台销售。
“我从网上进购的大部分无品牌表带的价格为25元-30元。”涂某某交代。印上华为的注册商标后,便以“大部分100元人民币左右”的价格销售出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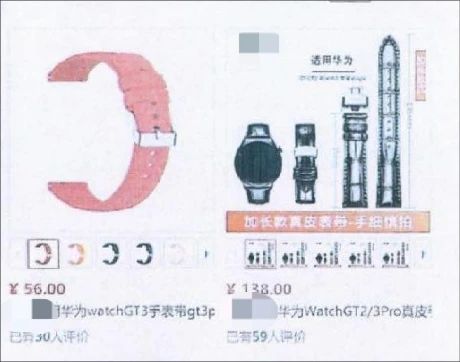
涉案网络平台销售页面
利益驱使,明知违法还参与
“我看身边的人都这么做,为了赚钱我也就做了。”张某乙说。2023年3月至5月,张某乙在明知涂某某、张某甲对外销售系假冒华为品牌手表表带的情况下,仍参与两人所经营的网络店铺的客服、售后、整理商品、激光打印华为商标、打包发货等事宜。此外,他还从上述两人处购入无注册商标的表带,以相同的手法印上华为商标后,通过自己注册的两家网店对外销售。
“销售假冒华为表带是违法犯罪的行为。”到案后,涂某某和张某乙如实说道。但为了利益,还是明知故犯。
检察机关经审查发现,涂某某假冒注册商标的非法经营数额共计人民币240万余元,其中自行开设店铺假冒注册商标的非法经营数额共计230万余元,参与张某乙假冒注册商标的非法经营数额共计10万余元;张某乙假冒注册商标的非法经营数额共计28万余元,其中参与涂某某假冒注册商标的非法经营数额共计16万余元,自行开设店铺假冒注册商标的金额非法经营数额共计10万余元。公安机关查获待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价值共计6000余元。
检察机关表示,涂某某、张某乙结伙,未经注册商标所有人许可,在同一种商品上使用与注册商标相同的商标,情节特别严重,其行为均已构成假冒注册商标罪。本案系共同犯罪。经虹口区检察院提起公诉,法院作出前述判决。(来源:澎湃新闻)
3.离职后将带有商标标识的视频保留转移至同行业其他公司账号上造成混淆,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

在离职后将自己的自媒体账号绑定至新公司线上店铺,账号视频中却还保存着带前公司注册商标的相关场景宣传视频,此行为是否侵犯注册商标的专用权?
基本案情
树某文化公司经营着一家瑜伽工作室,于2019年注册了“树下图形”“树样英文”标识注册商标,注册有效期为十年,商标核定服务项目为第41类的培训、教育信息、学校(教育)等。
陈某于2018年3月起担任某健身工作室的员工。2022年3月,陈某加入树某文化公司开办的瑜伽工作室,并将其自媒体账号(以“手艺人”的身份)绑定于树某文化公司经营的线上店铺。2022年11月21日,陈某从树某文化公司离职,回到某健身工作室工作,并将其自媒体账号绑定于该健身工作室的线上店铺上。
后树某文化公司发现,陈某的自媒体账号“学员案例”中有包含“树下图形”“树样英文”标识的图片和训练视频,这些图片和视频系陈某在树某文化公司工作期间制作、上传。在陈某自媒体账号解绑树某文化公司线上店铺转而绑定某健身工作室线上店铺后,这些图片和视频便随之展示在该健身工作室的“教练”项目之下。树某文化公司认为,其公司在健身、教育行业均具有广泛影响力,因陈某离职后侵犯公司商标的行为,导致树某文化公司短期内流失大量客源,且多数客户在某工作室办卡健身,其中存在高度因果关系,遂起诉至珠海市香洲区人民法院,要求承担侵权损失。
裁判结果
法院认为,虽然涉案图片和视频为陈某转职后自行展示于某健身工作室线上店铺,但在事实上会造成类似于将一个市场主体的宣传广告展示在另一个市场主体经营场所的效果,容易导致消费者误认为两个市场经营主体之间存在关联关系。因此,陈某侵害了树某文化公司涉案注册商标的专用权。因陈某已删除相关图片和视频,树某文化公司未提交证据证明其商誉受损,综合考虑树某文化公司商标的知名度、陈某侵权的具体情节、维权合理支出等因素,酌情确定陈某赔偿树某文化公司经济损失及维权合理开支共计2000元。
树某文化公司不服,向珠海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珠海中院二审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法官说法
珠海中院法官陈莹: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第四条第二款的规定,本法有关商品商标的规定,适用于服务商标。本案涉案两个注册商标均为教育培训类的商标,陈某在任职树某文化公司期间将制作的带商标的视频和图片上传至自媒体账号用于宣传,应当被认定为商标使用行为。离职后将带有商标标识的视频保留转移至同行业其他公司账号上,易造成消费者对两个品牌的混淆,侵害了涉案注册商标的专用权,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标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一条的规定,应承担停止侵权、消除影响、赔偿损失的民事责任。(来源:珠海市中级人民法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