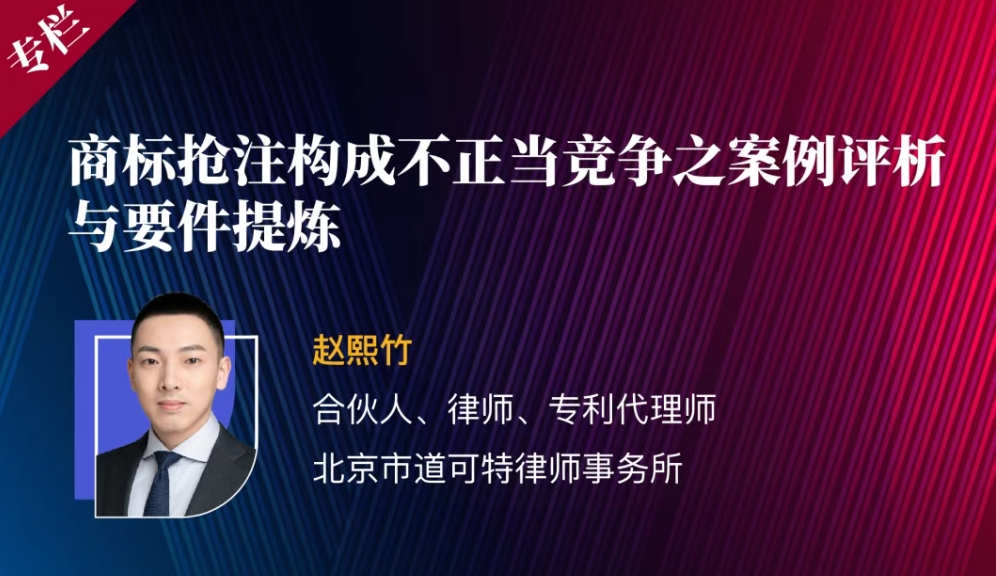
赵熙竹 | 商标抢注构成不正当竞争之案例评析与要件提炼
· 引言
一、权利人的救济困境:程序vs 效率?
二、适用《反不正当竞争法》予以规制的法律逻辑
三、典型案例评析与不正当竞争构成要件的提炼
· 结语
引 言
在经济全球化与数字技术叠加的背景下,商标已从传统的商品识别符号演化为企业核心资产与市场竞争的战略工具。与此同时,商标抢注(trademark squatting)逐渐成为侵蚀市场诚信、扭曲竞争秩序的全球性问题。
在中国,随着市场活力释放与品牌经济崛起,商标注册量连续多年稳居世界首位。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在近三年的《世界知识产权指标》(World Intellectual Property Indicators)报告中,均提及中国市场的商标申请数量在全球商标申请总量中的高占比。例如,在2022年的报告中,WIPO将全球商标申请总量的增加归因于中国提交的大量商标申请(sheer volume of trademark applications filed in China),并指出仅中国的申请数量就占全球商标申请年度增长的11.5%[1]。在2024年的报告中,WIPO指出中国的申请主体仍然是全球最活跃的申请人(Chinese applicants remained the world’s most active filers in 2023)[2]。
然而,高数量的商标申请背景下,“恶意抢注知名品牌”“跨类抢注公共资源”“抢注-维权商业化”等乱象频发,甚至形成灰色产业链。国家知识产权局数据显示,仅2024年上半年,国家知识产权局全流程打击商标恶意注册就高达20.5万件[3],折射出了规制抢注行为的现实紧迫性。
本文将以“制度困境—法律逻辑—典型案例—要件提炼”为脉络,系统分析商标抢注行为的不正当竞争认定路径,试图为优化知识产权协同保护体系提供智识参考。
PART.01 权利人的救济困境:程序vs 效率?
(一)途径:商标异议、无效宣告和商标撤销
中国的注册商标专用权是由行政机关授权的权利。因此,与此类权利有关的争议应当通过行政程序由行政机关予以裁决是基本共识。事实上,针对商标抢注问题,中国的实体法配套了相对完整的救济途径。其中,《商标法》第33条、第35条规定了商标异议程序,并引述了利害关系人有权提起商标异议申请的情形;第44条、第45条则针对已注册商标规定了商标权无效宣告程序以及利害关系人可以申请宣告商标无效的情形;第49条和第54条则提供了“兜底性”的救济方案——商标撤销:注册商标成为其核定使用的商品的通用名称或者没有正当理由连续三年不使用的,任何单位或者个人可以向商标局申请撤销该注册商标。
(二)现实:行政程序的三重时间成本叠加
如前所述,现行《商标法》设置的异议、无效与撤销程序,原本是为权利人提供分层救济路径,但程序叠加与衔接缺陷使其异化为维权壁垒。
1.商标异议:权利人的“第一个希望”
依据《商标法》第35条,对初步审定商标提出异议后,商标局需12个月(可延长至18个月)作出决定(虽然实践中审查周期已缩短);若被异议人申请复审或提起诉讼,程序将再延长1-2年。
2.无效宣告:事后纠错的“制度枷锁”
根据《商标法》第44、45条,对已注册商标提起无效宣告需经12-18个月行政审查,若当事人提起诉讼,维权周期将进一步拉长。此外,对于抢注超过五年的商标,权利人还需额外举证抢注人具有恶意或被抢注商标是驰名商标。更为严峻的是,无效宣告原则上仅具有“对世效力”而无溯及力(《商标法》第47条第2款为例外)[4]。抢注期间造成的商誉损害难以完全弥合。
3.撤销程序:使用要求的“反向制约”
针对“无正当理由三年不使用”商标的撤销程序,虽审查周期较短(9-12个月),但抢注者可通过象征性使用、关联公司授权等规避撤销,迫使权利人陷入“申请-撤销-再抢注”的循环博弈。
(三)缺陷:制度性延迟
根据2024年国家知识产权局《奋力推进商标事业高质量发展——国家知识产权局商标局2024年上半年亮点工作成效一览》工作报告[5]:商标注册平均审查周期稳定在4个月,一般情形商标注册周期稳定在7个月。
然而,针对抢注行为的行政救济程序却陷入“马拉松式”困局。数据显示,截至2024年,商标异议案件平均审理周期为10个月,无效宣告案件(评审案件)为10.5个月,若叠加行政诉讼一审、二审程序,权利人从启动维权到终局裁决需耗费2~3年,这期间还不包括送达、移案、当事人制造程序障碍(如申请裁判者回避、中止或延长举证期限等)等期限迟延。
这种“前端审查提速”与“后端纠偏低效”的悖反,客观上为恶意抢注者提供了“制度套利”空间——抢注商标一旦进入公告或注册阶段,即便最终被宣告无效,侵权人仍可利用程序空窗期实施搭便车、胁迫和解等行为,导致“正义迟到即正义消亡”。
(四)困境:程序完备性下的效率失衡
行政救济程序的复杂设计,本质上是对“程序正义”的恪守,但在商标抢注治理中却面临多重矛盾。其一,制度成本与维权收益的倒挂:中小企业维权成本(如律师费、时间投入)常高于抢注商标的市场价值,导致“理性弃权”;其二,程序稳定性与市场动态性的冲突:互联网经济下商标价值周期缩短,2-3年的维权周期可能导致维权成果丧失商业意义;这些困境暴露出单一依赖《商标法》框架的局限性——即便实体规则完备,若程序机制无法适配市场效率,仍将消解制度初衷。
PART.02 适用《反不正当竞争法》予以规制的法律逻辑
(一)实体规定逻辑——商标抢注的定性偏移:从确权到竞争工具
我国是大陆法系国家,因此争议解决的创新必然伴随着某项实体法律规定的锚定。《商标法》框架下,抢注行为多被视为“权属瑕疵”问题,侧重从注册程序合法性层面评价。然而,商标抢注并非单纯的“权利登记”或“权利授予”,其背后往往伴随攀附商誉、干扰对手经营、谋取不正当竞争优势等目的,此类行为已超出商标确权争议的范畴,构成对市场竞争秩序的破坏。因此,《反不正当竞争法》的介入,本质是将抢注行为定性为市场竞争工具的非法运用。
《反不正当竞争法》第2条规定,经营者在生产经营活动中,应当遵循自愿、平等、公平、诚信的原则,遵守法律和商业道德。本法所称的不正当竞争行为,是指经营者在生产经营活动中,违反本法规定,扰乱市场竞争秩序,损害其他经营者或者消费者的合法权益的行为。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条进一步明确:经营者扰乱市场竞争秩序,损害其他经营者或者消费者合法权益,且属于违反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二章及专利法、商标法、著作权法等规定之外情形的,人民法院可以适用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二条予以认定。
由此可见,《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二条明确了“诚实信用+商业道德”为内核的帝王条款。随后,司法解释围绕竞争关系[6]、商业道德[7]进行了若干条款的补充。确立了对“虽未违反专门法但违背诚信原则”的行为,可直接适用一般条款的法律渊源。这为商标抢注的竞争法规制提供了直接依据。
(二)必要性逻辑——《商标法》功能局限的实质补强
如前所述,单一依赖《商标法》治理商标抢注存在程序低效的困境。除此以外,商标行政审查的客观性特征(例如只能与在先申请或注册的近似商标进行比对、审查员无法主动发起申请人主观恶意审查等),也导致商标确权程序中存在申请人主观意图审查缺位的现象。对于已注册的抢注商标而言,权利滥用现象更是处于“失控”的状态。在多起商标抢注构成不正当竞争的案例中(后文有分析引述),抢注人利用发送侵权警告函、提起异议或无效宣告等程序反向胁迫权利人。
《反不正当竞争法》在治理逻辑上则恰好填补上述结构性漏洞。主要表现在:其一,《反不正当竞争法》锁定“损人利己”的主观恶意,评价行为人主观动机的非法性。其二,《反不正当竞争法》延展了《商标法》的法益保护范围,保护对象从“注册商标专用权”及其权益延伸至“竞争优势”。
因此,与《商标法》个案纠偏不同,《反不正当竞争法》可在整体上针对“抢注行为”进行评价,且从客观行为穿透至主观目的,为权利人救济提供了动态、综合的规则供给。
PART.03 典型案例评析与不正当竞争构成要件的提炼
(一)典型案例
案例一
上海企徒体育发展有限公司诉戈壁商学院(厦门)有限公司侵害商标权及不正当竞争纠纷案(以下简称“千人走戈壁”案,(2023)闵02民终3413号)[8](笔者代理案件)
【案情简介】
原告企徒公司是一家专注于体育赛事策划、运营及体育产品服务的大型体育赛事公司。原告的“千人走戈壁”品牌在户外赛事活动特别是“戈壁徒步户外赛事服务”上享有极高的知名度。
早在2018年,原告便获准注册了系列“千人走戈壁”商标,核定使用服务为第41类:体育野营服务、导游服务等。
2018~2020年期间,原告与被告戈壁公司曾合作经营“千人走戈壁”体育赛事。在此期间,戈壁公司在35类服务上,批量注册了“千人走戈壁”商标,指定使用服务包含广告、替他人推销等
2021年,原告在第41类服务上申请注册的“千企走戈壁”商标初步审定公告。同年,被告依据其抢注的“千人走戈壁”商标对企徒公司第41类“千企走戈壁”商标的注册申请提出异议。
【法院认定】
戈壁公司成立时间晚于企徒公司,且曾与企徒公司合作开展戈壁徒步赛事活动,知悉企徒公司涉案商标的知名度及其“千人走戈壁”赛事活动的商业价值,应对企徒公司的在先权利及市场劳动成果予以尊重,并在遵守法律和商业道德的前提下展开市场竞争。
戈壁公司抢先注册商标并以此对企徒公司正常的商标注册申请提出异议系戈壁公司实施侵权行为的一部分,旨在攀附竞争对手企徒公司及其品牌的商誉,设置障碍配合其他侵权行为,干扰企徒公司的正常经营活动,以攫取本应属于企徒公司的竞争优势,其行为具有不正当性,损害了企徒公司的合法权益,属于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二条所规制的不正当竞争行为。
【主要裁判结果】
赔偿企徒公司经济损失20万元。
案例二
“碧然德”商标侵权及不正当竞争纠纷案——2021年上海法院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力度典型案件之八(以下简称“碧然德案”,(2021)沪73民终204号)[9]
【案情简介】
1966年,原告碧然德公司于1966年在德国注册成立,自1993年起在中国陆续注册登记了“BRITA”“碧然德”等多个商标,并通过代理商、成立全资子公司进行品牌销售与经营。
2010年,被告康点公司注册成立,在多个网络平台上宣传和销售其“碧然德”滤水壶、滤芯等产品,在淘宝网页使用“德国碧然德滤水壶原装正品批发招商”等文字介绍,在微信平台以“碧然德”的微信名称开设网店经营销售。
被告在多个商品及服务类别上申请注册“碧然德”“德碧然德”“BRITA”等商标多达21项,还以其正在申请注册的“德碧然德”商标作为引证商标,请求宣告原告“碧然德”注册商标无效,并对原告正在申请注册的其他6项“碧然德”商标提出异议。
【法院认定】
原告的“BRITA”“碧然德”在经营过程中通过持续使用和宣传,已具有一定的市场知名度,其碧然德产品亦在中国饮用水优化产品市场占据一定的市场份额。
被告通过恶意抢注、滥用异议处理程序等行为损害原告在先权利,在相关类别上恶意抢注与原告注册商标相同、近似的商标,并以此为基础利用商标异议、无效宣告等程序,干扰、阻碍原告正常行使商标权利,其恶意抢注、滥用异议程序等行为是被告大规模、综合性侵权行为的一部分,服务于侵权的总体目的,其实质在于攀附竞争对手原告及其品牌的商誉、设置障碍配合其他侵权行为干扰原告正常经营活动,意在破坏原告的竞争优势,建立自己的竞争优势,具有明显的主观恶意。
【主要裁判结果】
赔偿原告碧然德公司、碧然德净水系统(上海)有限公司经济损失230万元。
案例三
“古北水镇”不正当竞争纠纷案——北京法院2022年度知识产权司法保护十大案例之八(以下简称“古北水镇案”,(2021)京73民终4553号,入库编号:2023-09-2-488-009)[10]
【案情简介】
2010年7月16日,古北水镇公司在北京市密云区注册成立,专为运营古北水镇景区设立。
2014年2月12日,小壕公司在北京市密云区注册成立。此后,小壕公司在第33类酒类商品、第25类服装等商品上申请注册“古北水镇”商标,并先后向古北水镇公司发送侵权警告函、提起商标侵权工商投诉,要求古北水镇公司停止在酒类产品包装上使用“古北水镇”商标等。
【法院认定】
小壕公司获准注册的涉案商标具有重大权利瑕疵,其申请注册涉案商标明显具有不正当性。
在2014年2月之前,“古北水镇”作为从事提供旅游餐饮等服务的古北水镇公司的企业字号及其使用在酒类商品上的商标,已在相关公众中具有了一定知名度,能够与原告形成相应的联系。被告理应对古北水镇公司的相关知识产权予以尊重并合理避让。被告实施上述行为的动机并非利用涉案商标开展正常的经营活动或维护自身的知识产权所需,而是意图抢占“古北水镇”商标资源,从而达到阻止他人使用该商业标志、攫取不正当商业利益与竞争优势的目的。被告注册取得涉案商标并行使商标权的行为,主观上具有明显的恶意。
【主要裁判结果】
赔偿原告古北水镇公司经济损失28万元。
(二)案例解构:基于司法实践的行为类型化
通过上述案例,商标抢注的类型可大致分为如下类型:
1.攀附商誉型:如千人走戈壁案。在这个案例中,被告的行为链条表现为:存在合作历史→抢注商标→滥用异议→干扰原商标使用,其主观目的是不正当地攀附、乃至攫取本属于原告的商誉和市场交易机会(注:被告之所以实施商标抢注行为,是基于在双方合作过程中知悉了原告商标的价值及其承载的市场商誉)。法院以“明知他人在先权益+商标抢注+程序权利滥用”锁定主观恶意,认定其行为违背商业道德,构成《反法》第二条规制的不正当竞争。
2.滥用程序型:如碧然德案。在这个案例中,被告的行为链条表现为:抢注商标→提起商标争议程序(如商标异议或无效宣告)→打击权利人。被告通过将商标确权及其争议程序工具化,其目的是实施对他人商誉和市场利益的抢夺。法院通过《反不正当竞争法》原则条款的适用,对被告的恶意侵害行为进行法律评价和直接处理,将“滥用商标行政程序”独立认定为不正当竞争。
3.跨界干扰型:如古北水镇案。在这个案例中,被告的行为链条表现为:跨类抢注商标→发送侵权警告函→提起恶意投诉。“跨界干扰型”的行为模式与“滥用程序型”近似,均表现为商标抢注后对真正的权利人实施打击。但“跨界干扰型”的不同之处在于,“跨界干扰”的抢注人更为隐蔽。在认定不正当竞争时,需要以具备竞争关系作为前提,而“跨界”恰恰成为抢注人抗辩“不具备竞争关系”的常见理由。法院通过穿透行为人主观目的,立足“损人利己”与“市场资源争夺”双重要素,认定被告的行为构成不正当竞争。
(三)商标抢注构成不正当竞争的要件提炼:四维评价体系的司法生成
基于案例裁判规则的归纳,商标抢注构成不正当竞争需满足以下要件:
1.主体要件:竞争关系的广义解释
认定标准:不要求直接同业竞争,只要抢注行为可能攫取或削弱他人竞争优势,例如“古北水镇案”。
在该案中,北京知识产权法院作出了如下认定:“竞争关系的广义化,是反不正当竞争法本身变化的结果。反不正当竞争法由民事侵权法发展而来,起初仅仅保护竞争者利益,但在其发展过程中,其立法目标已经由保护竞争者利益不断向保护消费者权益和维护公共利益方面拓宽,由单纯的私权保护不断向实现市场管制目标发展。这就使不正当竞争行为的界定不限于同业竞争者之间的竞争行为,而拓展到非同业竞争者的竞争损害。”可见,《反不正当竞争法》的立法目的从“保护竞争者”转向“维护竞争秩序”,需以动态市场视角界定竞争关系。
2.主观要件:恶意目的的穿透识别
核心要素:明知或应知他人在先权益+损害竞争对手的故意。在举证中,可通过抢注数量(批量注册)、时间节点(合作结束后立即抢注)、后续行为(滥用程序)等间接证据推定恶意。例如“千人走戈壁案”。
在该案中,厦门市湖里区人民法院和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均确认了被告和权利人之间的合作历史,并结合抢注行为的时间节点以及抢注后的商标异议行为,认定不正当竞争成立。
3.行为要件:竞争工具的非正当运用
行为类型:包括但不限于抢注商标、滥用异议/无效程序、发送侵权警告函等。商标抢注之所以构成不正当竞争,其违法本质在于行为人将商标申请及《商标法》赋予表征权利人(在本文中即指向基于抢注行为而“虚假”获得注册商标专用权的主体)的程序性权利进行非正当运用,以合法形式掩盖“攫取竞争优势”之非法目的,构成对《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二条“商业道德”的实质违反,如“碧然德案”中程序权利商业化。
4.结果要件:竞争秩序损害的多元化评价
本文列举的三个案例中,基本上囊括了利用商标抢注及其程序性权利实施不正当竞争导致损害的情形。其中直接损害可表现为:权利人商誉贬损、市场机会丧失,如“古北水镇案”中品牌扩展受阻、“千人走戈壁案”中权利人的市场份额遭受非法挤压。间接损害则表现为:消费者混淆、行政/司法资源浪费,如“碧然德案”中,权利人应对无效宣告和异议程序的经济性支出等。从三个案例传递出司法启示来看,竞争法益涵盖“正当经营免受恶意干扰”的消极权益。损害结果不要求实际损失,程序滥用导致的资源耗损即可构成竞争秩序损害。
结语
商标抢注作为市场竞争中的“制度性寄生行为”,在挑战传统商标法的程序正义框架的同时,也“逼迫”司法实践探索多元规制路径。通过《反不正当竞争法》的能动适用,现有的裁判案例逐步反馈出了“竞争关系泛化认定—主观恶意穿透—抢注行为工具化评价—损害推定”的逻辑,为遏制抢注乱象提供了更具效率与弹性的治理工具。未来,随着数字经济的深化发展,商标抢注的形态将更趋隐蔽与复杂,唯有通过“立法补漏、行政协同、司法创新”三位一体的动态治理,才能实现知识产权保护与市场自由竞争的再平衡,在彰显了中国本土治理逻辑的创新同时,为全球商标治理贡献中国智慧。
注释(上下滑动阅览)
【1】WIPO,
World Intellectual Property Indicators 2022
【2】WIPO, World Intellectual Property Indicators 2024
【3】国家知识产权局商标局,《奋力推进商标事业高质量发展——国家知识产权局商标局2024年上半年亮点工作成效一览》
作者:赵熙竹
编辑:Sharon



